王国维(1877年12月3日-1927年6月2日)
“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,那就是自杀。”这是阿尔贝·加缪说过的一句话,在他看来,判断生活是否值得过本身,便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。
死亡是那样容易,但生命的思虑却常常很沉重。
“口鼻塞满淤泥,身下是一片水迹,世界寂静悠远,没有任何声息。”研究王国维的学者周宁是这样来形容他离开时的画面。王国维本人连自杀的原因都不屑于解释,只是检验官在他衣袋里发现一份简单的遗书,开头有16个字: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,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。”那是怎样的“时变”?怎样的“义”?
93年了。回顾如今存在于各种文献中的王国维,那一天,他以一种颇显凄凉却又可能是最严肃的方式,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死去,而此后被各个时代记起。有人说在王国维之死中看到自由,没有人可以再侮辱他,有人说在王国维的自杀中看到奴役,附着在自杀之上的任何宏大意义都显得荒诞。只是在他自己的理解和认同中,彼时彼刻的死亡或许是与其心中秉承的道义最相契的结果。
以下内容经商务印书馆授权,整合自《人间草木》第四章。

《人间草木》,周宁著,商务印书馆,2009年10月。
原文作者|周宁
他的死是一个谜: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”

陈丹青油画“(清华)国学研究院”局部,左起第三为王国维。
1927年6月2日上午,还有两天就是那年的端午节。颐和园的园丁听到几丈外一声水响,刚才还在鱼藻轩独自抽烟的老者,转眼间跳入湖中。园丁急忙赶来将人救起,仅几分钟,竟去了一条命。湖水很浅,王国维被水下的淤泥堵塞了口鼻,瞬间窒息身亡。
死亡是如此容易。车夫还在颐和园门口等他出来,家人还在家中等他回去,可他作为陌生人,已经全无知觉地匍匐在昆明湖边,口鼻塞满淤泥,身下是一片水迹,世界寂静悠远,没有任何声息。检验官在他衣袋里发现一份简单的遗书,开头16个字似乎说明死因:
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,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。”
仅此而已。
名人用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不鲜见,但王国维不一样,他死得很轻松,甚至不屑说明自杀的原因。
死亡可能是没有意义的,这是死者的立场。生者却不同,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空旷的真实。王国维溘然长逝,他究竟为何选择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,至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题。
孤立在梦境边缘的鸟:宁静的美好总是不堪一击
1925年,王国维接受了清华学校的礼聘,此时,他名义上仍是溥仪的“南书房行走”,伴逊位天子读古书。可1924年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,溥仪出走天津,“流亡”的那天,王国维随驾出宫,“未敢稍离左右”。仁义深厚,也到此为止。
离此人海,躲入书斋,天荒地老处与二三素心人商量学术,原本是闲适从容的。清华研究院待遇优渥,每月400大洋。奉旨入京之时风光无限,但他虽食朝廷俸禄,却领不到实际的薪水,常常举债度日。
在清华,王国维教授经学、小学、上古史,每周三个课时,其余时间潜心于自己的研究,日子平静而悠长。每天早晨起来,太太帮他梳理发辨,这是一天开始的沉静庄重的仪式。有一次太太劝他剪去发辫,他竟表现出少有的恼怒。那条纤细的发辨,是他身份、情感、理想的象征。
王先生故去之后,学生们回忆当年课上,印象最深的细节是他每转过身去,垂在脑后细长的发辫在眼前轻轻扫过,与黑板上的殷墟文字一般悠远而梦幻。
对于真正的学者,学术就是生活。除了从事研究、上课之外,在办公室或家中接待来访的学生,还有远道而来的友人,一年后陈寅恪搬来清华园作邻居,王国维有时去他那里坐坐,隔一段时间总要进一次城,逛逛琉璃厂,淘古玩,访旧书。
然而,这一切都是短暂脆弱的,几乎让人来不及品味,人像孤立在梦境边缘的鸟,若有所思,片刻之后便惊飞了,划破凝固的空气。
这个世界的宁静美好总是那么脆弱、虚幻,不堪一击。1926年中秋刚过,长子潜明在上海病逝,王国维痛惜万分,短暂的好时光从此结束了。20年前莫氏夫人逝世,王国维悲痛难解,写下许多悼亡诗,如今老年丧子,更是悲痛欲绝。一切远未结束,半年之间,祸不单行。王国维准备“哀死宁生”,却与多年至交、亲家罗振玉失和,最终导致绝交。生命不仅是痛苦,还让人受尽屈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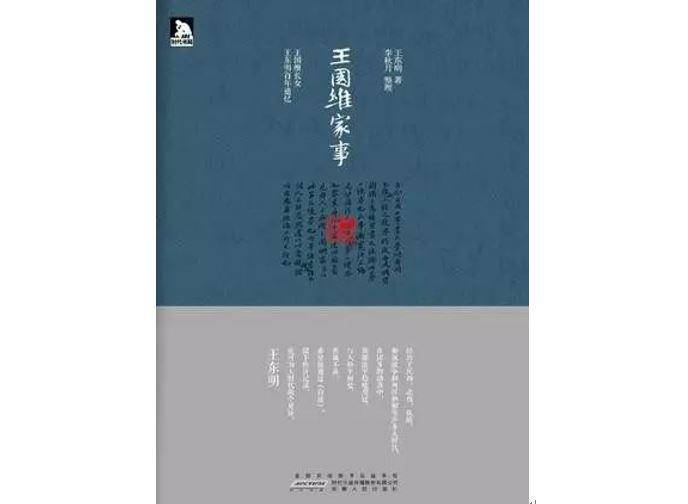
《王国维家事》,王长明著,安徽人民出版社,2013年3月。王国维长女王东明的百年追忆。
有所惧大于死
国维在岁末的沉郁哀痛中度过50寿辰,阴郁的1927年新年在北伐战争的鼓角声中到来,哀痛中又加上了恐怖。北伐军攻陷北京,什么事都可能发生,他们这些前清遗老,恐怕性命难保。
陈寅恪来访,与王国维谈起“中国人之残酷”。一周之内,军阀张作霖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钊(1927年4月6日),革命党处决了湖南大儒叶德辉(1927年4月11日)。都是不祥的预兆,连梁启超这样的新派人物,也准备再次流亡日本。王国维绝望了,生的恐惧大于死的恐惧。
世界残暴疯狂,已经难以理喻。梁启超邀请王国维同去日本避难,王国维拒绝。18年前曾与罗振玉一家流寓东瀛,他不想重复那种生活;陈寅恪劝他到城里躲躲,他的回答简单到“我不能走”;学生邀请他去山西避乱,他问:“没有书,怎么办?”王国维谢绝了所有的好意,不是因为他不能走,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走。此时,他感到恐惧与厌倦的,不是北京这一个地方,而是整个现世。
有所惧大于死者。王国维生路已绝,死意已决。清华园里人心惶惶,1927年春季学期草草结束,计划提前于6月1日正午开师生叙别会,然后放假,大家各奔东西。叙别会前一天,遗老朋友金梁来访,“平居简默”的王先生,那天竟“忧愤异常”。他们谈话中说起颐和园,王国维感慨:“今日干净土,惟此一湾水耳。”
尘世的最后一夜在平静中睡过,早晨起来,一如既往。他坐到那里,由太太梳理发辫,似乎也没有想过,这是在为另一个世界束装。八点钟到研究院,商量下学期招生的事,然后便雇车去了颐和园。师友门生家人,没有人在他身上看出任何异常。人生原本这样,每一天都可以生,每一天都可以死。
最后的阳光下,王国维抽了一支烟,呼吸之间,烟火明灭,像他那脆弱敏感的生命。万古恒常,短暂的一生不过像是这支纸烟。
随即便是一声水响,在宁静安详中,永远消失。
不过是一介书生
王国维投湖那天是那年端午节前两天,人们纷纷将他的死于屈原联系到一起。轻生死者重道义,这是中国的传统,不过王国维倒从未表白自己的死与这位文化先贤有什么因缘。
如果王国维之死若真与屈原之死有某种关联或承继,那么,这个关联点或承继点,一定隐蔽在王国维精神深处。
三十岁前后,王国维经历了人生的双重转型:一是学术上的,从西学转入国学;二是生活上,从独学转入用世。朦胧中,他或许已意识到某种奇异的“宿命”,隐约暗示在他所著的《屈子文学之精神》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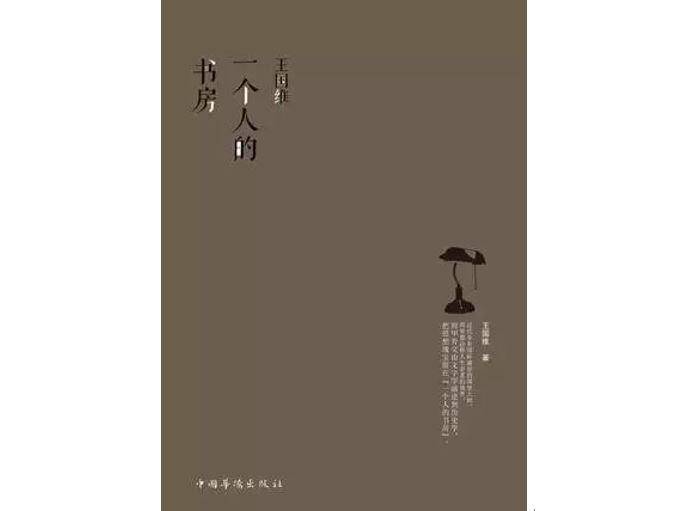
《王国维:一个人的书房》,王国维著,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6年1月。
王国维说屈原一方面洁身自好,有所不为,这是南人的超脱,另一方面又辗转激愤,为所不能为,这是北人的执著。集南人北人品性于一身,无法既超脱又执著,纠缠不清,执拗不开,总是死路一条。屈子投江,似乎是不可避免的“宿命”。
这是否也是他的“宿命”?
1908年,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屑眷北上,开始了“南人作北人”之旅。本无心政治的他却在因缘际会中与政治纠缠不清。
他经罗振玉举荐入宫任“学部总务司行走”,实质至多是一名图书管理员。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,王国维入了遗老行列。四年后从日本回来,王国维在上海凭自己的学问谋生,不料罗振玉又帮他谋得个“南书房行走”,再次入宫。
王国维既无明确的政治理想,更无自如的政治能力,无辜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一种政治败局中。王国维生平得罗振玉提携,感恩常使他“失去自我”;尴尬的政治人生,多与罗振玉的“挟持”有关。冯玉祥逼宫,废帝避难天津,王国维产生了莫名的“道义感”,竟与罗振玉等遗老相约投神武门御河殉清求死,后来被家人看住了,没能成就“君辱臣死”的大节,却入了遗老行列。他想象自己是个有操守、念旧情的人,君辱臣死,从此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噩梦。
说到头来王国维不过是一介书生,书生本性注定的政治人生,一定是失败而痛苦的。他是一个只有道德理想而没有政治抱负的人,执着于理想,不肯苟合于社会。政治的污浊最终吞食了他的热情,起初厌倦,终于绝望,溥仪出走天津,王国维并未随行,多少算是解脱,但也并不轻松。
王国维当年看出屈子文学精神的内在分裂,却看不出这种分裂必然导致一种文化以及一种“文化所化之人”精神分裂的悲剧结局。
王国维自沉之故,在个人人格的分裂,也在塑造这种人格的文化传统的断裂。在王国维身上,有屈子文学精神的宿命,也有孔子文化精神的宿命。屈原与孔子,都生在一个败落的时代,都代表一种理想化的道德立场,都以“生死抗争”的方式试图匡扶政治拯救世道,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
儒家思想是乌托邦式的,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历史中被政治权利伪装成意识形态,成为似是而非的肯定现存秩序的思想。帝王政治与儒家理想之间本质上的对立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,形成一种千年文化幻觉。在这种幻觉中,儒者自以为可以通过为帝王谋家国,实现个人的道德理想。可实际的下场是,或为帝王豢养驱使的走狗,或为帝王逼困抛弃的丧家犬。
只有人的道德,没有非人的道德
王国维的死是完全的被动之死,死亡是一种逃避。
有人在王国维之死中看到自由,死亡之后,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再奴役他再侮辱他。
有人在王国维的自杀中看到奴役,自杀不是勇敢,而是懦弱,附着在自杀之上的任何宏大意义都显得荒诞。
苏格拉底临终时说:“此刻,我去死,你们去活,谁的去处更好,只有神知道。”哲学家的态度似乎较为开明,柏拉图认为不可责备那些因命运坎坷、受尽屈辱艰辛而自杀的人。休谟也是有条件地为自杀辩护,人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。
但是,在尊重人、人性、自由精神的启蒙哲学中,自杀是一种软弱的犯罪。康德将伦理学的基础建立在自由前提上,明确谴责自杀轻蔑存于人性中的人道。
在尊重人、人性、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前提下,理性的确很难为自杀辩护。自杀可以以情感感动人心,却不能以道理说服人脑。一个民族精神强大,不在心,而在脑。终日靠感动过日子的民族,心智上不成熟、意志上不坚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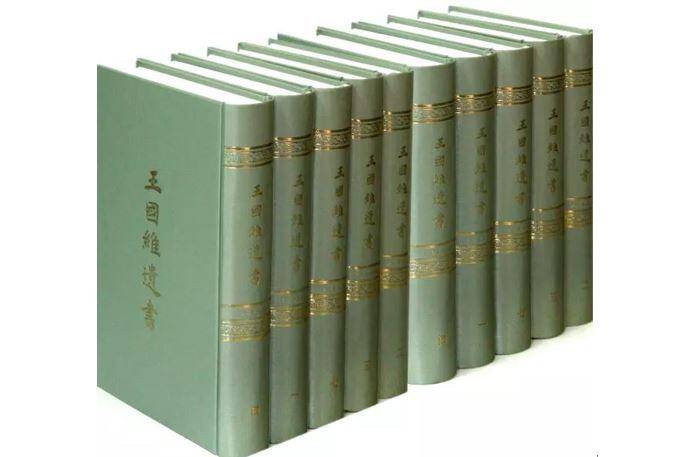
《王国维遗书》,王国维著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1年8月。
王国维在一个失败的时代死去,在无聊的时代又被记起。浅薄短暂的感动之后,人们沉不下心去深入思考他们实验过的生死的意义。
当年梁启超反对“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”王国维之死,“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,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……”可是,所谓中国古代道德的意义是什么?人生于危乱,忧民忧君,又无能为力,“与其苟活,不如殉死”。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的气节是有了,但真可以“以死救末俗”吗?
自杀对个体生命是不负责任的,对社会道德与政治生活,未必也真负责任。真诚纯正的君子们都殉了死节,最终的结局只是“地下太平”了,天下危乱依旧。这个世界会好吗?
王国维的自杀,其意义可能是审美的,但未必是道德的,绝对不是政治的。人可能为死亡之美所感动,但未必能从中获得道德的振奋;即使能感到短暂的道德振奋,也未必能作用于政治实践,进而改造社会创造历史。
就此而言,加缪的立场或许更加值得赞赏,生活中孤独、苦难、堕落、危险无处不在,死亡也随时随地发生,但我们始终要充满开朗的激情,睁着眼看死亡与光明,让激情中有热爱、感激、信念、欢喜……
个人高尚勇敢的生存境界在“苦难与阳光”之间。
人,只有人的道德,没有非人的道德;只有活的道德,没有死的道德。思想是痛苦的,但思想是唯一的途径,引领我们走出心灵之夜。